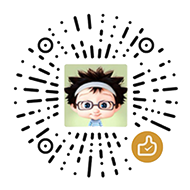01
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在北京上大学。
那时学校有不少课也停了,每天晚上我还坚持正常去自习,回来路过小卖部的时候,会买一包类似辣条的零食,很辣,但好吃。
忽然有一天,我发烧了。自己在宿舍了挣扎大半天,见没好转,没敢连累舍友同学,只好去了校医院自首。校医院一听是发烧,说他们无能为力,让我去北医三院做一下检查。
于是我叫了个出租车,跟司机说去北医三院。就当快到医院的时候,司机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问:“你不会是发烧吧?”
我说:“是发烧”
司机大叔一下急了:“你赶紧给我下去!钱我不收了。”
于是我被撵下来独自走到医院。那一刻心开始凉了,原来这个世界如此灰暗,危难时人与人如此冷漠。自己有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
02
北医三院检查的过程很快,就是抽血,等验血报告。但接下来等待的过程就长了了,这个“长”不是客观上的半个多小时,而是内心的煎熬,就像过了好几个小时。
有一种犯人等待宣判结果的感觉。是死刑还是无罪释放,就等着后面那张薛定谔的检查报告。等待过程中,开始有些同学给我发短信询问情况,我一条都没敢回。
整个医院也没什么人,偶尔有救护车进出,安静得可怕。在发热门诊的地方,坐着若干和我一样的人。每个人都沉默,不相互搭话,因为你不知道旁边的人里,会不会有真的感染者。
03
终于验血报告出来,我被判定为无罪释放。
于是我又叫了个车回学校,上车时我跟司机说:“我发着烧”。
司机大哥说:“没事,能从里面出来的人,都没事。”
忽然感觉,这个世界又明媚起来了呢,还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啊。
04
回到学校,我们被安排在校医院隔离观察。
隔离头三天我的高烧还一直不退,退烧药吃到第三天,医生说不能再吃了,自己扛着吧。于是在第三天的下午,我烧到昏睡了过去。
醒来时已是晚上,忽然发现喉咙很痒很痛,我拼命地喝开水,再拼命地咳,最终咳出了一个大血球。血球咳出来之后,我感觉整个人重生了,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
原来这么多天的发烧,是喉咙发炎引起的。再往细想,难道这一切就是因为之前每天一包的辣条造成的?
05
最终我在校医院住了半个月,一日三餐学校全包,吃好住好。不过就是孤独,一人住一间病房,不能串门。陪伴我的只有一台收音机,一本英语6级词汇,和只能发短信的手机。
那段独处的日子挺像一场修行,自己的内心好像变得特别平和。出院后不久,我之前挂了几次的英语6级考试也顺利通过了。
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周迅的《看海》是那年电台的热播歌曲;也时不时会想起那两个出租车司机,他们一前一后的出现,就像文学上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