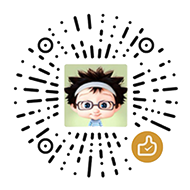和大多数人一样,胡迁的名字对我来说很陌生。好奇心作祟,驱使我去看了看这位自缢青年背后的状态。幸运的,我找到了一些真实且打动我的东西。鉴于大多数人不会去关注一个停更的微博,我想把它们贴出来。
毕业后,我知道跟他人争论任何问题都是无效的,互相只能靠话语权来使对方屈服。
每次有什么活动,最烦听到“人脉”“资源”这两个词。《小城之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此国电影也没什么真正艺术水准上的长进,人脉和资源通到南极上又有什么用?二十年后猜火车都2了,这里还是“方言,乡村,熊孩子”三大宝。其实这些活动的酒局上不只能多认识人,还能吃屎呢。
有一次在三里屯遇到个火山女主播搭讪,她说帅哥你是做什么的,我说纯文学,她说什么文学,我说文学,她说网络文学?我说不是。她说那你一个月得赚十万吧,我说没有,她说五万总有吧,我说不可能,她说两万呢?我说看收成。她说这会儿他们给我刷了几个火山,一个三千快。我说你厉害。
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几个月写封信过去人回“恶心不恶心”。今天蚂蚁微贷都还不上,还不上就借不出。关键是周围人还都觉得你运气特好,CTMD。
最近一直在跟一个朋友喝酒,喝了一个月,他教我呲妞,费老劲了也没用,某个关键时刻从面前横穿一辆超跑,他说:“开这个就分分钟的事儿了”。真给力,毕业那年,去接那个狗逼恐怖片拍,现在我也改装个排气筒横穿马路了。之后的几年还得攒钱,把自己第一部电影版权买回来,两辆超跑钱,以拍艺术片的收入来看,不去贩毒很难做到。
当那些人拍着网剧写着商业片剧本胡吃海喝换车旅游的时候,走过来说你运气真好啊真羡慕啊,我真想取出我珍藏的凿子和斧子。
一个多月前看徐浩峰更新的博客,我盯着那句“一念之愚,千里之哀”愣了半小时。不是因为那会儿“千里之哀”了,是意识到这句话时,一切都已不可改变,早些年即便知道这个道理,也不会信,现在哀也没鸡毛用。三月份在剧组时就听说了好几个自杀的,当时还没觉得什么,等我自己的电影在半年后没了才发现,都他妈完了。
胡迁也曾尝试过主流的方法希望改善收入:“2015年,我在股市5120点那天满怀期待地入市,至今全仓,但仓已经快没了。”这忽然跟我的经历联系到了一起。那天我叫的uber回家,uber司机和我说:这辆车就是这几个月的股票赚回来的,5000点绝对没到头,你也应该尽快入市。这两件事就像是硬币的两面,而现实中人们选择性的只鼓吹一面。
网上还有一篇他的简单访谈:
问:有人说你的作品会让人感到丧气、绝望的负面情绪很多,你对此怎么看?
胡迁:那你去问问他,每天醒来,临睡前,或者上班时去饮水机接水的时候,只要他有一瞬间反思过自己,就知道每天都在美化自身的生活。朋友圈发点东西在自己身上贴标签,或者手机里攒了几百张照片等着什么时候给人看。我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真正可贵的事物,是在世界的夹缝中,而不是悲观在世界的夹缝中。认识到这一点,也许会对整个生命的秩序有由衷的感动。
问:你心中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胡迁:现在我二十八岁了,十几岁时还奢望理想的生活状态,现在不这么看待这个问题了。压根不存在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你要选择具有哪种缺憾的生活。
问:这本书中,有很多故事都给人很真实的感觉,有哪些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吗,或者你真的经历过?
胡迁:每个故事会有一个源发点是真实的,故事发展的情感逻辑是真实的,所有的细节是真实的。你可以把它们看作真实的故事,我觉得会发生,而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比我写的更有力量。你得使尽浑身解数才能扯开点什么,才能看到一丝自认为的美好之物,但之后,只要你懈怠了,灰暗会重新堆积。《大裂》里面写的不是青春,是中国大部分大学生,或者叫专科生。人们总是讨论白领群体、底层、既得利益者、创业者等等人群,这些标签下的人在若干年前还是青年时,人们又都统一美化成青春,这是一个错误的定义。赖在宿舍每天打游戏,无所适从,不明所以地谈恋爱,这个中国庞大的青年群体,不叫青春,这里面有很复杂的东西,复杂得跟加缪的《局外人》一样。
看完这些,整天饱受现代媒体浸淫的我们,心里会冒出一些词: “理想主义” “抑郁症” “看不开”。经历了那么多自杀事件,人们依然要么是无礼指责“想不开”,要么是浪漫化地想象。理想主义者在当下这个操蛋的社会生存,需要更多的忍耐,妥协和技巧。指责或评判每个自杀谢世的人,都是挺轻薄不道德的,我们并不知道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黑暗。
最后用一句胡迁的话结束,这是他点评自己访谈稿时说的:“这篇访谈少了最后一句,我逼逼这么多就是为了说这句话——生活中,大部分逻辑都只是一个问句:‘你这么做就是为了多捞点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