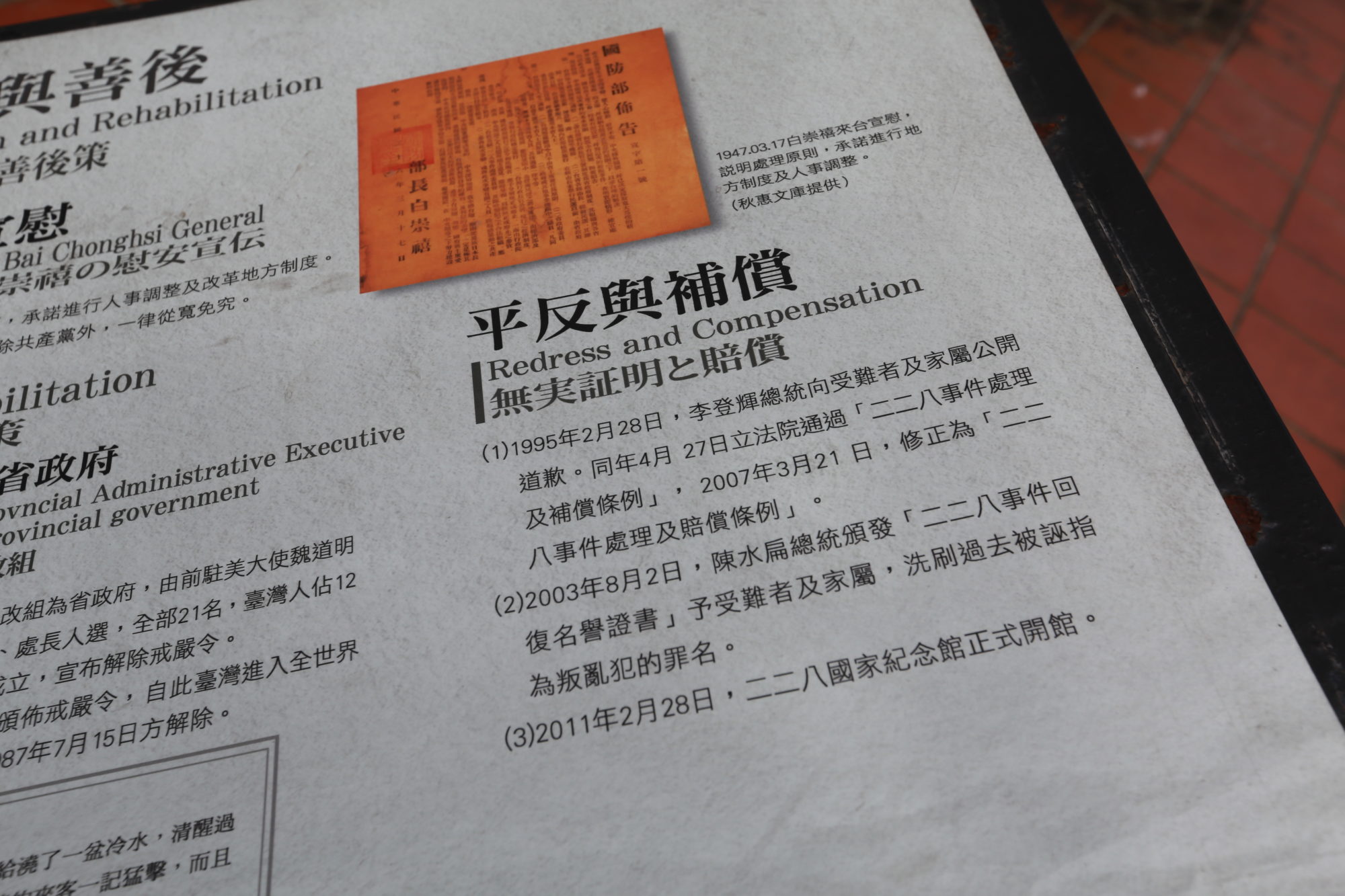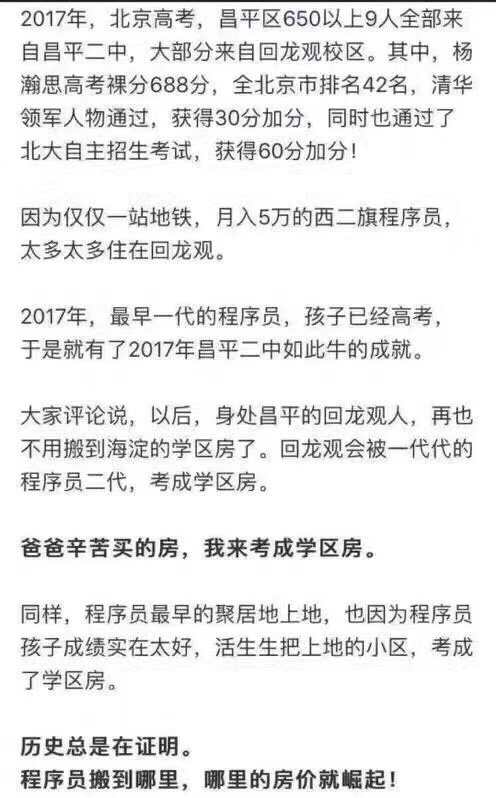在2008年左右,那时中文网络里的大V是韩寒、南周、老罗等等,以公共知识分子居多。
他们部分以个人姿态出现在互联网,但背后都有着专业的知识储备和职业训练。因此产出内容的覆盖面以及专业度都有所保障。用现在的概念说可能类似PGC。另外一方面,他们产出的大量文章内容,在多年后我们却记不起多少,脑海中只是保留着他们的IP形象。
这说明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普通人对于“某个内容”并没有太深记忆,再大的热点总会被更新的热点所取代。而网络上产生的评论类作品,大多又不能像著书一样,将作者自己固定在文化经典的某个位置,所以日后的观众对这些大V的认知又是从零开始,新的观众并不会觉得他们有多权威。
新平台的崛起,总会伴随新的网络领袖和大V。由于曾经的大V没有办法像优秀作家一样,把自己固定在共同文化经典的某个位置,所以他们维持自己知名度以及号召力的办法必须是不断地继续产出。而许多功成名就的人未必有动力继续做这样的努力,比如韩寒要搞赛车,要拍电影;老罗要办企业,做手机。而留下来的人也要面临社会环境,社会话语风格等等的转变,困难不少。
到了后期的大互联网平台,都以UGC为主。人人都是作者,人人都是导演,人人都是主播…这种将曾经显得专业的职业降低门槛,造就了内容供给侧的繁荣。但UGC年代的网红与过去不一样的是,大多并未收到过专业的训练和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他们的优势大多是新奇,贴近群众,以及共同营造出的多样性。
于是我们会发现如今的网红、热点更替会越来越快,因为非职业的选手,其产出内容创意会单一,涉及社会面太窄,很难满足观众对新鲜的渴望,许多人红的那一刻已经用完“毕生”所学及体验。所以能否从单打独斗的自媒体和个人,提升为专业的小团队甚为关键。
想持续保持新内容产出,要不扩大内容覆盖领域,要不就在垂直领域深挖死磕,比较网络用户已经无比的大,服务一小部分人就已经有不错的收益。对大量非专业出身的UGC时代大V来说,基本都只能做后者。
所以在新的网络上,我们能感受到许多年轻的90后,00后,他们在某一方面的教育训练和知识储备比曾经的七八十年代的青少年好很多。这得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但也少不了就是内容的繁荣以及获取内容的便捷,看看B站上各种各样的教程就可以知道。
但同时我们发现“公共”开始消失,即在极具个性化的各种兴趣点之外,有些曾经与大多数人相关的话题空间,消失了。这种消失除了来自于官方的打压控制,也来自于大众的不感兴趣。表现出来一方面是媒体行业不断势微,一方面日常热点大都是偶像娱乐。
媒体一大作用是设置公众议题,我们打开报纸,看到从头版排到最后的一条条新闻话题,实则是告诉我们,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而日常缺少了这些公共的讨论,其实让我们缺少了一块缓冲摩擦的地方。于是造成大部分的人,平日要不不出圈,只在自我小天地里玩;要不某天被一个重大事件迫使出圈,就会产生“怎么还有这样的不同声音”的感慨。
如今的网民大多就是这样隔离地生活,“公共”消失了,“公知精英”消失了,我们只和与自己特别相配的人玩,“部落效应”也随着越来越严重。这如果是在一个理性的良好环境里,倒也看似问题不大,毕竟在这个倡导个人自由意志的年代,必然鼓励个人价值的多元化,个人发展也理应是丰富多彩的。🌈
然而对一个并不完善的社会来说(事实在这个地球上,也没什么国家能称得上是完美的),完全把公共空间拱手让出是危险的。它的威胁也许是多年后才到来,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只关心自己圈”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公共纽带的消失,让大家彼此很难团结在一起,凝聚大的反抗力量。
希望在日常中,我们都能分出一些精力去关心他人理解他人,而不要遇到意见不一时,就割席站队。
人生能多样化地发展,多样化地选择,这些美好需要建立在某些“共同”的理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