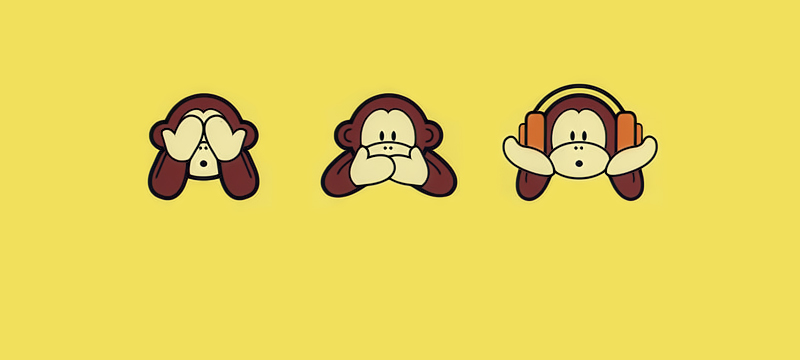2013年10月27日,美国著名音乐人地下丝绒乐队的前主唱兼吉他手Lou Reed去世,享年71岁。作为当今摇滚界首屈一指的元老级人物之一,Lou Reed的音乐历程从六十年代至今横跨接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当代音乐文化的万千气象。在离开地下丝绒乐队后,Lou Reed的单飞生涯在三十多年内几起几落,最终修成正果,成为全球亿万乐迷顶礼膜拜的教父式人物。在中国,他被大家亲切的称为老李。(感谢Bob,小丑先生和Charawu共同完成本期节目)
第066期:窗外飞象,对影成三
多伦多大学一项研究发现:单身的恐惧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很多年轻人放低自己择偶的标准,或者坚持跟一个“错误的人”在一起。研究人员指出,有20%的人公开表示对单身充满恐惧感。这种深刻的恐惧,让他们愿意保持一些不那么好的情侣关系。 说到底这种恐惧,就是对孤独的恐惧。刚刚过去的双11,单身的人们在这一天不一定能告别单身,但一个娱乐化的节日,一场狂欢似的血拼,至少可以让人暂时告别孤独和孤独带来的恐惧。这个世界充满了令人分心的事物及娱乐,每当我们有一点闲暇时,我们就去寻找某种形式的娱乐,做为逃避自我的方法,只因我们害怕孤独。
今晚平淡的观影
电影《横道世之介》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当今社会推崇的优点。甚至电影里提到其特质之一:开朗,也并非常人印象里谈笑风生,风趣幽默的那种。总结起来,主人公最大的特点是他的单纯。
电影里主人公横道世之介的经历很普通,故事没有高潮,甚至可以说没有“冲突”。他最终成为了一个摄影师,并在35岁时在地铁拯救一位女士而牺牲了生命。但这两个能被当今社会作为“卖点”的地方,电影里都没有特别表现,只是一带而过。
故事虽平淡,但坚持看完还是觉得温暖感动。我觉得其实人如果能像上帝般观察着一个普通人的一生,甚至不用那么久,就像电影用2个半小时去经历他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有让你感动和尊敬的地方。
现实是:没有人耐心听一个普通人讲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急于表达自己,愿意倾听的人少之又少。 而你希望别人耐心倾听你的观点和看法吗?最好先问问自己成功了没有。这个社会就是那么唯结果论。
一个很单纯随和,对事物充满好奇心,不靠显摆自己的经历来加强其社会地位的人,往往是这个社会容易被忽略的一位弱者。但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生过客,不妨珍惜。
第065期:就这样漂着
张楚在他的文章《永远的租客》里说到:“有一次我朋友把她的助理从成都送到北京,看是不是适合当我的助理,是一个女孩,我们在咖啡馆见了面,我们聊了一下,出门走在胡同的时候,她突然跳到路边的台阶上,觉得很好玩的看了我一眼,我觉得她还象个天真的孩子,我就让她回去了,这儿实在是太辛苦,让自由的天真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吧。”看完这篇文章,自然回想起自己过去在北京的租客生涯。如今从北京漂到广州,虽然仍是租房,但不会像在北京有明显漂的感觉,即便买了房也是漂着的感觉。广州给人感觉温暖很多,我想不只是天气的缘故。
晚安
大懒堂:佛山一夜

其实不管从哪方面看自己都不像是一个听Rap音乐的人,在高中的时候我也基本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很难想像会和粗口音乐有所关联。这和昨天坐我身边的18岁女生不一样,她读的广州一所中专,她说自己是早几年对人生感觉很灰的时候,受朋友推荐听上了大懒堂。细究起来这也许和我隐藏得较深的本质有关。总结起来就是:我从来都有机会混入这个社会认可的上层,和那些所谓精英一样。但每当人生遇到这样的契机时,我内心就会抗拒退缩。一种强烈的草根性让我很抗拒去做一些改变,而希望待在一个相对屌丝的环境,也像是歌里唱的“屋邨仔”吧。
昨天演出时身后一位哥们喊:“老了,跳不动了,前面的朋友坐一会吧”。不管是台上的,台下的,大家都老了。年轻时心中那团火,还能保持多久呢。原本我并没有计划去佛山看大懒堂内地首演,但去了之后觉得真是无憾。原本以为自己会和以往一样安静的看完演出,没想到真的和他们一起唱了跳了起来。那种感觉很释放,原本自己个性里也有这样一部分特质吧,但从来很少释放表达过,也受益于昨天周围没有认识我的人。
演出回来,看到佛山很多学拳的孩子;还有中国散打冠军与泰拳冠军比赛的海报,票价不菲;路边还有一些咏春拳馆,这让我隐约感受到了叶问,和黄飞鸿的余风。并回响起那句歌词:“要真正表达你本质,至系最积极既武德!”。








第064期:午夜失眠曲
有一阵总是失眠,一到睡觉点,就开始胡思乱想,天马行空,怎么也停不下来。后来辞职赋闲在家,就很少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似乎我的失眠并非和工作压力相关,如果说真有压力,那也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现在想来更多可能是工作后白天不再有胡思乱想的时间,只有晚上躺下了,才偷得自己天马行空的时间与空间。所以这期电台是给失眠的自己,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有失眠的困扰,那这期电台也同样送给你,希望它能有催眠的疗效。
第063期:生活从来不在别处
身未动心已远总是看起来美好,就像生活在别处。旅行, 不过是城里人下乡,乡下人进城,各自寻找别处的生活,梦一场远方再打回现实。没人不爱旅行,只是我们匆忙间错过的又岂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就能弥补的。生活从来不在别处。生活只在此处。回过头看此处的风景,那才是属于你自己可以细细品味一生的美。
第062期:请在音乐放完后提问
不少人推荐一本书「学会提问」,坦白讲,这本书我看到三分之一已经有些看不下去。这类方法论的书要摆在10年前大概还会有些兴奋甚至求知若渴,但现在,看这样的书就像是做脑力训练。其实问问题实在是很容易的事。当然问问题跟会问问题还是有差别的。不过如果真要问的话,先问问自己,为什么要问?好多时候我们提问已经忘了提问的初心是什么,不过想问倒对方而已。单纯有兴趣的提问会让谈话得以继续,一个好的提问者首先一定是个好的倾听者。
第061期:竖琴女声
很早就想整理一期竖琴女声的专题,可惜除了Joanna Newsom,竟然没能找到第二个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竖琴女声。大多都是像Yasmeen Amina Olya和Cécile Corbel这样,都是世界音乐和民歌的风格,好像竖琴精灵般的音色,天生就适合这类音乐,虽清澈舒服却少了惊喜。但也有Dorothy Ashby这样的爵士竖琴探索,以及当今最喜欢的年轻一代的独立竖琴女声:Joanna Newsom。
三亚印象
原以为三亚既然已是著名旅游城市,应该还是建设得不错,没想到在市区转了一天感觉很失望。倒不是要求它如大城市一般繁华,但主要像公交等城市基础建设都仍是非常不完善。说到吃海鲜,也不比我老家好。倒是蓝天和沙滩还是挺不错的。





回来查了查原来三亚才几十万人,的确很小。但因为独特的资源,搞得如今当地房价那么高。外面的有钱人想进驻,当地年轻人却想离开。其实感觉告诉我住在那并不好,但有钱人也说了:买房不是要定居,只是为了每年度假。这和当地光鲜的酒店与破旧的城市建设形成的强烈反差带给我的感受一样,这种反差让我没有对三亚产生留恋与不舍。



被生活分裂的破碎想法
最近半年生活有很多改变,最大的当属没什么个人时间。虽然抓住一切碎片化的时间做自己的事,看似很努力,但效率不高。还是喜欢安下心来,干屈指可数的事。
另外对自己将来该过怎么样的生活,也天天挣扎。已经无法象很多人一样老老实实一辈子当上班族,真心体会到有些事你经历了就回不去了。
过了三十岁后再也没感觉人生漫长,容自己掌控的时间似乎都能算出来,比如在现在公司每年其实就干两件大事。不过伴随的是牺牲掉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如果某天不上班,是否能干得多些呢,是否能在养家糊口和“干我想干”之间做到平衡。
在对生活周边的一些新鲜事物兴趣上,变的有所迟钝,明白学无止境,时间有限,只想把时间集中在人生重要的主线上。倒不是不学习,而是更希望在现有能力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挖掘看用这些能力能干什么。
这点似乎还和我近几年的社交思路一致,比如对能否发展更多圈子,认识更多朋友已无所谓。反而希望能更多了解以前的朋友都怎么样了,要能再相聚,就更好了。
第060期:弄堂里石库门
微博上看到有朋友提到上海的石库门,和所有大城市的传统老建筑一样,石库门在上海就如同四合院在北京,已经所剩不多,剩下的也都奇货可居。小时候有幸在上海住过一年石库门,像我这样健忘的人,对石库门的记忆其实已经有些残缺。我家住在三楼,爸妈住三楼的一间大屋,而我则住在楼顶的亭子间里,虽然那会才小学5年级,但那种一伸手就摸到天花板的压抑感觉到现在还记得。早上起床只能坐在床上,有时候会迷迷糊糊忘了想在床上站起来,结果就撞到头了。亭子间里一扇窗开向石库门的院子,另一扇就是亭子间标志性的斜天窗,那时的我,喜欢躺在床上望那一小格天空,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原来幸福的大小跟能看到天空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图片来源:Rachel Gouk
石库门的记忆

微博上看到有朋友提到上海的石库门,和所有大城市的传统老建筑一样,石库门在上海就如同四合院在北京,已经所剩不多,剩下的也都奇货可居。
小时候有幸在上海住过一年石库门,像我这样健忘的人,对石库门的记忆其实已经有些残缺。我家住在三楼,爸妈住三楼的一间大屋,而我则住在楼顶的亭子间里,虽然那会才小学5年级,但那种一伸手就摸到天花板的压抑感觉到现在还记得。早上起床只能坐在床上,有时候会迷迷糊糊忘了想在床上站起来,结果就撞到头了。亭子间里一扇窗开向石库门的院子,另一扇就是亭子间标志性的斜天窗,那时的我,喜欢躺在床上望那一小格天空,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原来幸福的大小跟能看到天空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亭子间跟爸妈的大屋由一小截竹梯连着,每天爬完三层木楼梯还要再爬上竹梯才能到我的亭子间。那三层木楼梯几乎是一年四季照不到光的,梅雨季节里总有挥之不去的发霉的味道,走起来又嘎吱作响。我还依稀记得二楼有扇门总是半掩着,里面黑乎乎的,每次放学回家,爬到二楼,我都会下意识的跑快几步,总担心那扇门背后会突然钻出来什么东西。后来高中时期玩《生化危机》,每次开一扇门的过场动画,总会让我想起石库门时期二楼的那扇门。
由门得名,自然石库门建筑的门楣部分是最为精彩的部分,装饰也最为丰富。可惜小时候的我对石库门最重要的这部分记忆几乎为零。对那时的我而言门就是门而已,从来不曾好好抬头多欣赏一下。只记得进门,穿过一小块天井就是一楼大厅,已经被改造成几家人共用的厨房,穿过大厅是一块不算大的院子,院子一角还有一口小池子,但那时的我很少到院子里去玩,一来整栋楼没有和我同龄的小伙伴,二来作为外来的小孩,刚到上海在学校被上海的小孩称作“乡下人”,性格上已经变得拘谨内向了很多,回到家从来就是宅在家里,很少再下楼活动。
弄堂还算比较宽,一侧有一条细细的水沟,曾经见过有些人来这里倒夜壶,我们住的石库门一楼有个茅厕,所以倒也一直没用过夜壶。但我一直不清楚水沟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也一直奇怪,有人往里面倒夜壶,为什么会没有异味。弄堂上空常常会挂满各家各户晾晒的衣服被子,层层叠叠,在风中招展,有时会遇上一些还在滴水的,穿行其中,总要小心避开那些水滴,就像在玩横板闪避过关游戏。弄堂口有个卖茶叶蛋的老人,也卖臭豆腐,上海的臭豆腐跟湖南臭豆腐完全不同,外表是金黄的,虽然都是闻着臭吃着香,但上海臭豆腐的臭味会相对淡些。那时我很喜欢吃弄口的那家臭豆腐,蘸上甜辣酱,想想都会流口水。
对于石库门的居住感,王安忆在《长恨歌》中描绘的淋漓尽致:一旦开门进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出现在了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好多年没再回上海,有机会回去要去看看曾经住过的永安里附近的弄堂,不知道那里的石库门还在吗?对于儿时居住的记忆,也许只有在重游故地时,有些回忆才能更清晰的显现出来。
配图来自:丸子
雪糕不解夏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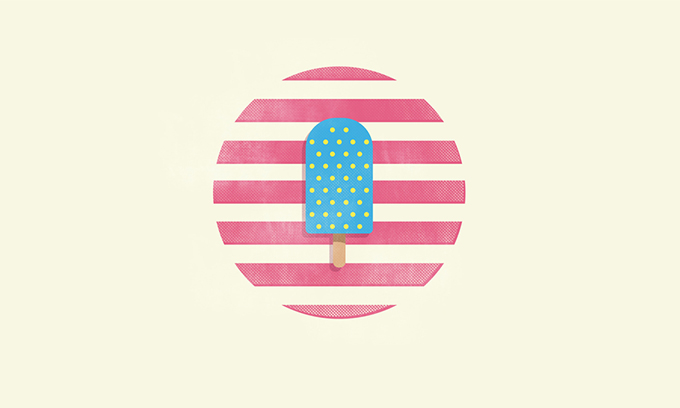
Kuuva是我电脑上一款随机换桌面的软件,今天突然给我换上了上面这张图,这才让我想起来今年夏天连一支雪糕都没有吃过。虽说冰激凌还是吃过2、3次,但明显吃的欲望越来越淡了,即使在最热的天气,也只是想喝点冰水而已。
就在几年前,每年夏天还都会去批发一堆雪糕冰激淋填满冰箱,每天不吃一两支总觉得不爽,下班回家路上买支雪糕边吃边走还会自我感觉比周围那些没雪糕吃的人幸福一些。而现在,虽然逛超市的时候,也会在冰激淋柜前流连,看看又有哪些新奇的雪糕,Fab的订阅也会常常在夏天应景的发来各式各样冰激淋的照片,但看过后仅仅止于欣赏,极少再有购买的冲动。
大概年纪越大,心态变得平和,体内环境也开始变得平和,不再像年轻时非得要外界刺激才能解除烦燥。对口味的追求也趋于平淡,简单的冰水已经好过讲究口感,口味丰富,外型吸引的雪糕。不过想到爸妈60多了,还是习惯每年夏天都要囤雪糕,难道是自己的心态已经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