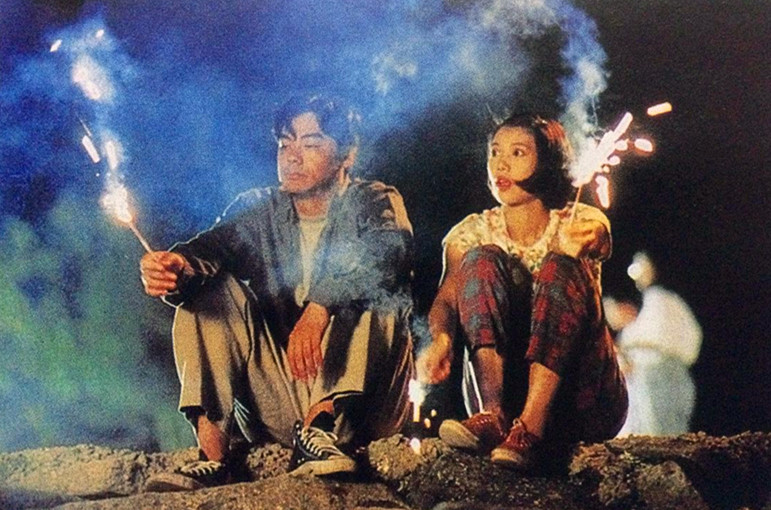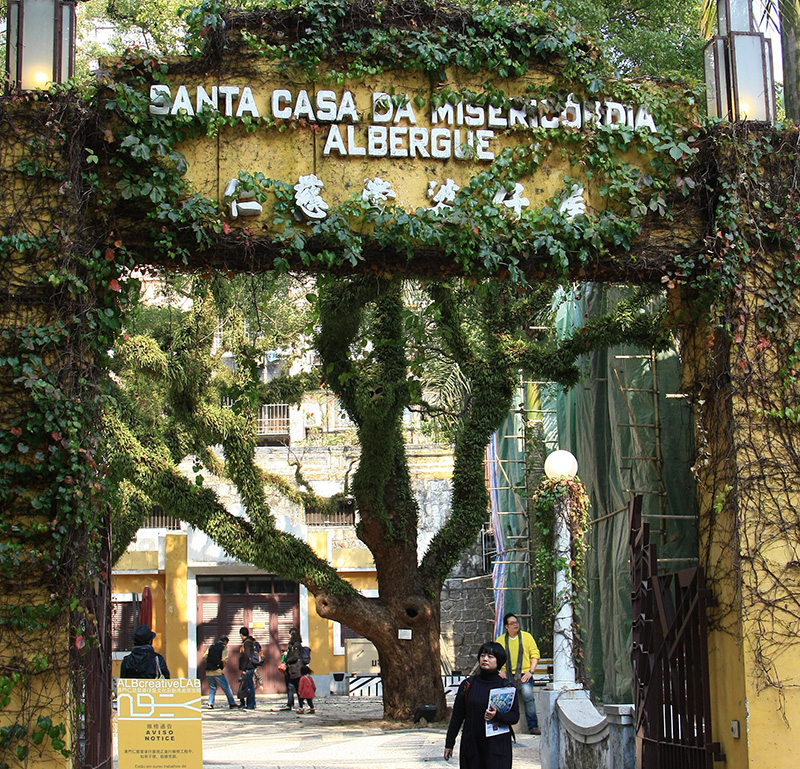2009年的春天,上海海事大学一位30岁的女研究生杨元元,因为学校拒绝她的母亲住她宿舍,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表面上看这件事只会让人想到教育制度,想到现代人的心理承受力等问题,但回过头看整个故事,你会发现让你不寒而栗的其实是她母亲对她的“情感勒索”。
美国心理医师苏珊•福沃德(Susan Forward)是这样解释“情感勒索”的: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操纵方式,和我们亲近的人用它直接或间接地威胁我们;如果我们不顺从他们,他们就会惩罚我们。不幸的是,在“孝道”的外衣下,“情感勒索”在中国处处可见。
杨元元的故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父亲早逝,从小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母亲是一家军工厂的工人。在她短短的三十年人生中,母亲望春玲一直以母爱和孝道的名义操纵着杨元元。女儿想报考大连海事大学,望春玲以考武汉大学可以省些路费为由,阻止了女儿做出这一选择。从女儿大三起,因军工厂拆迁失去住处,她到大学投奔女儿,和女儿挤在一张床上居住,从此两人形影不离。女儿考上了小城市的公务员,因她希望女儿去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而放弃。女儿30岁了,渴望爱情,亲属也劝她考虑女儿的终身大事,她却说,“我们楼上三十好几没结婚的多了”。女儿考上上海海事大学的研究生,虽然她每月有987元的退休金,但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跟着去,和女儿同住宿舍。女儿两个月的研究生生涯里,从未参加任何一项集体活动,每次只是默默地跟在母亲背后,听她母亲说话。
没有朋友、没有梦想,没有自己的生活。杨元元唯一拥有的就是母亲,以及无穷的挫折、孤独、憋闷、自卑、屈辱和道德枷锁。这是一个完全看不到未来的故事,于是死亡也就顺其自然的发生了。
情感勒索者索要的是比通常物质上的敲诈勒索复杂得多的东西,可以是对方的关怀、付出等情感,也可以是金钱、时间和精力。打着爱的旗号,情感勒索者的目的是关系中的亲密,而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