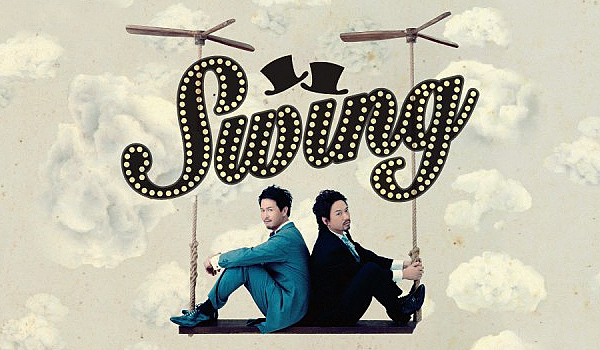香港流行组合swing,即将举办他们的解散演唱会,再次解散。粤语流行乐在经历了辉煌的时代后,慢慢萧条,swing则是这一阶段我在粤语流行乐少有的珍藏。听他们的音乐,不会有对华语流行乐的抗拒,只想惬意的沉浸其中,忘了时间。他们的再次解散,让粤语乐坛又暗淡了不少。那边见吧。
身份
也许我们害怕死亡的最大理由,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我们相信自己有一个独立的、特殊的、个别的身份,但如果我们勇于面对它,就会发现这个身份是由一连串永无止境的元素支撑起来的:我们的姓名、我们的传记,我们的伙伴、家人、房子、工作、朋友、信用卡……我们的安全感就建立在这些脆弱而短暂的支持之上。当这些完全被拿走的时候,我们还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么?
—— 西藏生死书
腹黑
三个月前,我们开始在家里养了几条孔雀鱼,挤在一个小圆形器皿里。每天给它们喂吃的时候,就会争着挤到水面上来抢吃的,很热闹。国庆假期的时候,由于我们有事外出几天,没法喂食,回来发现已经死了几条鱼。也不知道是饿的,还是晚上太冷,热带鱼受不了,那时还没有暖气。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剩下的几条鱼也不幸陆续翻肚了,一时间弄得自己有点伤感和愧对生命。最后发现只剩下了一条鱼。当时觉得也许我们养得不得道,不会照料,所以虽然看着这剩下的一条有点孤单,但也决定先不再买新的鱼了。天气也越来越冷,就等到家里暖气来了再说吧。
在这等待暖气的一个多月里,每天晚上气温不断下降,我们也没怎么加倍悉心照料这条鱼,只是每天喂食。但惊奇的发现,这条鱼在同伴全都离开之后,竟然生命力顽强地撑到了现在,独自一人熬过了几十个寒冷的夜晚,不由得让我赞叹。同时脑子里忽然又冒出一个很腹黑的想法:不会是这家伙把其它鱼给斗死了吧?它现在似乎吃食物都不抢了,慢慢吃。
弄得我们很犹豫是否应该再给它找几个同伴呢?
第026期:安乐而非快乐
有个朋友喜欢把快乐挂在嘴边,逢人便讲说“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快乐才是最重要的”。你问他到底什么是快乐,他会说天天有好玩的,有美食好酒,活得开心就是快乐咯。的确,快乐有太多近亲,开心,放怀,高兴,快活,狂喜,兴奋,喜悦,在生活逼人及时行乐的大势下,很容易令人忽略了快乐的母亲,其实是安乐。心境不能安乐,又如何能保证飘忽无常的快乐呢?
《给弟弟的安眠曲》
周末看了《给弟弟的安眠曲》,整个片子平淡无奇,主要讲的是一位姐姐对自己没什么出息的弟弟,一直无法割舍的故事。影片中的弟弟就是一个长不大,酗酒,闹事,看起来无所事事的大叔。所以这让姐姐的付出看起来是那么的没有理由,很多人都说“这个弟弟完全不值得可怜”。
故事中间倒是说出了电影的主旨。话说电影中这位“姐姐”的女儿小春,是舅舅给起的名字,也就是那位“弟弟”起的。当时为什么要找这位傻瓜舅舅给起名字呢?原来是“姐姐”去世的老公当年的意思,她老公当年说:这位舅舅从小到大,就没什么出息,大家都讨厌他,他也从来没做过什么值得自豪或者他人赞许的事情。他的一生似乎总是浑浑噩噩,看似多余。所以把这个起名字的重要任务交给他,让他也能自豪一下。
后来的故事也印证了这位舅舅真的为此自豪不少,他经常跟人说:“小春这个名字是我起的啊”。我想这真的是他认为一生中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了。回想起来,“姐姐”的那位去世老公真是高境界,在给自己女儿起名的事上能想到这样做,毕竟这件事真是没什么大不了,虽然叫小春土了一点,但也无碍女儿的成长。重要的是它足以让“弟弟”一生增添不少快乐,人生多了几分意义。
看现今当下:你要是真的贫困呢,还有人救济你一下。如果不是,又没什么作为,那基本都怪你自己不努力了。谁会关心这样的“弟弟”生活怎么样呢?谁会像那位姐姐的老公,在意他们的内心感受呢?谁会为这样的“弟弟”拍一部电影呢?
那又怎样
有时候,人们任相同的问题害他们好几年惨兮兮,而他们其实可以说:“那又怎样。”那是我最喜欢说的话之一。“那又怎样。” “我妈不爱我。”那又怎样。 “我丈夫不跟我上床。”那又怎样。 “我功成名就但却依然孤独一人。”那又怎样。 我不知道在我学会如何玩这一招之前是怎么度过那些年头的,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但是一旦会了之后,永远都不会忘记。——安迪沃霍尔
我总是被孤独吸引
比尔波特说“我总是被孤独吸引”。喜欢独处,“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其他人在一起,而是因为我发现独处有如此多的快乐。有时候,我愿意躺在树下凝视着树枝,树枝之上的云彩,以及云彩之上的天空,注视着在天空,云彩和树枝间穿越飞翔的小鸟,看着树叶从树上飘落,落到我身边的草地上。我知道我们都是这个斑斓舞蹈的一部分。而有趣的是,只有当我们独处时,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万物同在。”
跟随比尔波特寻访中国隐士的足迹,阅读《空谷幽兰》的过程,就像是在寻访自己内心的清净之地,对于同样喜欢独处的我而言,是再舒服不过的旅程。
记得第一份工作时常会出差,我就喜欢一个人待在宾馆大大的房间里,放上自己喜欢的音乐,让声音渗透宁静的夜晚,呼吸难得静谧的空气。晚上总是舍不得入睡,好像不多待会,就是一种浪费。
独处让我变得安详。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可以无拘束地天马行空。那会写过很多小诗,也哼过不少突发奇想的旋律,记下了一些,遗失了大多数。
换了工作以后,不再有出差时那样美美的夜晚,工资是在上涨,独处的时间却渐渐变少。只期望每天工作完能早早回家,更多时间享受两个人的独处,有更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
而生活中独处的乐趣,“不是离群索居,而是因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与大家更为和谐地共处。对于城市中的人来说,置身滚滚红尘滔天,每天面对无数欲望颠沛,若能保持自持修行的坚韧,遵循品德和良知,洁净恩慈,并以此化成心里一朵清香简单的兰花,即使不置身于幽深僻静的山谷,也能自留出一片清静天地。”
外来禅
看《空谷幽兰》和Zen Blog的时候,总有些隐约的怪感觉,特别今天看到Zen上一篇英文的老子语录,更是觉得有些怪异。好像现在的中国,讲道家讲老子讲禅的人反而不如国外。当我想找一些当代关于禅的故事或者解读时,不经意的,竟然都是老外的东西。文化是输出了,但我们自己还记得么?
中午几个同事还在聊说韩国人把什么都说成是自己的笑话,有人当成笑话,有人觉得文化产物不该分国界,也有人认真的,但有时候想,韩国人这样一闹,也不见得是坏事,说不定别人不提,我们自己都快忘了呢。就像越不容易得到的东西越觉得珍惜,一个道理,像韩国这样都是外来文化的国度,反而会珍惜来之不易的文化产物,而总是沾沾自喜于千年文化底蕴的我们,反而不把文化当回事,要不就是另一个极端,过度包装,拿来卖钱。
开菠萝记
国庆老爸从老家带了个大树菠萝过来,就是菠萝蜜。菠萝蜜隋唐时从印度传入中国,称为“频那挲”(梵文Panasa 对音),宋代改称菠萝蜜,沿用至今。北京这边常见的那种菠萝我们老家管叫“麻子”。而菠萝蜜才是我们那边常说的菠萝。菠萝蜜是世上最重的水果,不大好带。这只到达北京时已经散发阵阵清香,正是待剖的时候。
先一刀劈两半,里面的果肉一下都暴露出来了。
接下来要把一个个金黄色的包从粘粘的纤维中挖出来,挖的时候最好带个塑胶手套。不然最后洗手的时候很麻烦,太粘了。
解剖完毕,成果如上。这么一个菠萝有几十个包可以吃,有些大的菠萝能够有100多个包的,真是够你吃的。菠萝蜜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碳水化合物、糖分、蛋白质、淀粉、维生素、氨基酸以及对人体有用的各种矿物质…具体的请自己百度一下。
菠萝蜜全身都是宝,吃完每个包的黄色的果肉,里面的果实也是可以吃的,一般用煮花生的方法,直接放热开水煮熟,即可以吃用。好的果实吃起来是粉粉的感觉,实在是美味之极。但如果长芽了,就基本不能再吃了。
全身都是宝,那大树菠萝的叶子有没有什么用?菠萝树的叶子是我们当地包“籺”(籺的发音为,粤语就念类似微博的@,如果是普通话的就念hé,用全拼和搜狗输入法就很容易打出来了)的好材料,可以令籺的味道更清香,增强口感,也给籺提供更充足的营养。以前每年春节,奶奶就要自己在家做籺,就会提前叫我和我爸在单位里的菠萝树上摘一大堆叶子带回去。后来奶奶腿脚不行了,不再自己做了,我们春节前才少了件事。
后海的疯婆子
国庆期间去了趟后海,虽然后海早已不是当初的感觉,但还是没想到变成这样。从最初的安静,到后来乱了点,我感觉也只是酒吧增多,拉客的开始多起来而已。近日去那一看,发现这俨然已变成一个挺大众化的景点了。当地针对这个国庆假期,路边搞了很多美食小摊,也吸引了许多的旅游团,喧嚣得跟其它的景点一样。然而后海这个地方其实是承受不了太大的客流量的,道路人流拥挤,地面脏乱便不可避免了。
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发现一个四五十岁的北京妇女,站在路中央喊着什么,于是过去听了一下,大概意思是这样:大家快来看我这个疯婆子,我就是个疯婆子,北京的形象就跟我一样,我们的家都被你们糟蹋啦,我能不疯吗…… 这位大妈没有立个牌写点字,所以在这么喧闹的路中央喊,其实很多人也没听出她是干嘛的,大家依然在两边走过,没怎么停留听她说。
更多游客的到来会给当地收入增加不少,政府还是希望把后海,南锣鼓巷这些小众景点推广出去的。如果你愿意把那的房子转手,当然能拿一大笔钱,换个地方买个豪宅。但如果你希望还在那个地方活成以前的状态,估计是比较困难了。至于什么更重要则是因人而异,看你是什么人吧。
想想诸如丽江这种景区,最初去旅游的一批人里,有的人回来只是很有兴致的向朋友推荐介绍,而又有很多条件不错的人在那里看到了商机,事情便发展成后来的样子。
教主之死
6号早上,风尘仆仆往卢沟桥赶的路上,偶然想起好几天没看手机报了,也没上网,整个假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陪家人游。拿出手机,看第一条手机报,一下就被焦点新闻中乔布斯去世的消息惊呆了,愣了一下,没回过神,往上翻,又确认了下是哪天的手机报,6号,消息说是昨天,那就是5号去世的,很快翻到那条新闻,看完还是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意外,突然有种一个时代终结了的莫名感受。好像没有心情再看别的新闻,胰腺癌,其实也算不得突然吧,当时就有很多人猜到了这个结局,但真正发生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些恍惚。抬起头,公车正在四五环之间一条不宽的路上穿行,车速很快,窗外树木的影子快速地在靠窗的乘客身上移动,满车人安静地随着车厢规律地晃动,大概这里面没有多少是用苹果的吧,这个消息离这辆飞奔的车很远,远得好像它发生在另一个叫做互联网的虚拟世界。
不是果粉,比起乔布斯对苹果的贡献,其实更欣赏他对皮克斯的贡献,要是没有乔布斯的慧眼和胆识,没有他财力上的支持,也没有今天的皮克斯。
第二天两个人躺在床上看电视,新闻里在说乔布斯的死,家那位一脸震惊,我才意识到之前忘记跟他说了。觉着几天不上网,和一手新闻都脱节了。真是生命无常,人生苦短。新闻里回顾着56岁的教主乔布斯的语录: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的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第025期:江湖的蓝调之夜
在江湖酒吧看了一场蓝调演出,现场录了些音,依稀应该能听到酒吧的喧嚣背景。酒吧里听蓝调是很迷幻也很对味儿的一件事,你会不自觉地跟随节奏晃动,散场时,却好像一首歌也没记住。
所谓误解
吴念真见面会上说,他不理解为什么很多大陆的朋友谈起台湾政治来兴致勃勃,谁都能说上个所以然来,揣测台湾民众的想法。他们都只是通过电视看过许许多多的片段而已,大部分从来没去过台湾,也没有在当地生活过。背景的差异的确造成很多看法的片面,还有误解。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照着自己期望的样子去想象而已。
正如见面会结束后,我们在书店里看书,翻到一本写香港音乐文化什么的书,名字忘了。随手翻的一页有“LMF大懒堂”字眼,这是一个我很欣赏的前香港说唱乐队。但那页书主要不是讲这个,那是一位香港的作者,很有自我批评跟反省的精神,文章主要表达的是香港乐队的文化性没有大陆的好。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他以前有一次来北京逛唱片店,看到一首歌叫什么地安门吧。他顿时觉得太吊太牛啦,竟然有胆量去用一个“地”字,来表达“天” 安门的对立面,实在太有种,太让作者为之一振了!
我顿时觉得很可笑,那首歌是什么我忘了,反正不是左小的《左小祖咒在地安门》。我是觉得,这位作者在看到“地安门”这个词,连歌词和歌曲都没接触到的前提下,就从歌名YY出这首歌太吊了,更多的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期望而已。如果他对北京了解多一点,他会知道其实北京真有“地安门”这个地方,那也许他可以稍微冷静一下,听完歌再做判断。
万一歌里唱的是“我爱北京地安门”这类,你又情何以堪呢。看来对事物的很多看法,往往只是当事人内心的投射而已。
他们问吴念真
两周前,吴念真新书发布会,来了小二百号人。整个采访很简单,基本就是吴老先生独角戏。以致我觉得少了点趣味,因为少了点突发反应和即场发挥,感觉只是讲了些准备好的故事。最后的观众提问环节倒让我有些感想。
第一位提问的女生说:“她很喜欢吴先生,专程赶来,她老师拜托她一定要拿到签名回去。然后她看了《一一》,觉得里面吴先生的角色就是自己的白马王子…诸如这些。”虽然我也认同电影《一一》里吴先生的角色演得非常不错,但实在没想到能与“白马王子”这个词扯上联系,角色给人的感受也与这相距甚远。不过这也罢了,萝卜青菜。只是觉得为什么国内很多这种提问,非得在开头表达自己多么热爱对方,对方对自己多么重要。这位女生说自己专程赶来,主持老六调侃道,是不是从利比亚赶过来。结果那女生只是说从北京赶过来。晕,这里哪位不是从北京赶过来呢。接着她表达了自己多么的热爱吴先生,很有意思,有时我觉得这种对偶像的表白:在某种场合,似乎不只是对偶像说的,似乎还是向周围的如我这样的群众说的。我没有她那般热爱吴先生,很惭愧…
之后一位男生再接再厉,问了《一一》电影名字的来历,吴先生也说不清楚,反正传说很多吧。那男生回应道:自己跟《一一》的摄影师交流过,估计认识。自己还了解了很多关于《一一》名字来历的传说,其中有6种比较靠谱,今天听到了第7种比较靠谱的…诸如此类。我刹时间又感觉这位仁兄的问题是否得到解答其实无所谓,重点是我们这些群众是否听清楚了,他认识摄影师,他知道很多种一一名字的来历。我没有他那般了解,又很惭愧…
其实最后一位男生问的问题还有点意义,但是不好回答。他让吴先生比较一下两岸城市年轻一代的特点。我大概记得吴先生说:感觉现在的大陆青年比以前自信多了,另外觉得这边还有人那么关注以前的老电影,还会看很长的文章,实在不可思议,在台湾已经很少了。台湾的年轻人最关心的是他们处于一个什么阶段,现阶段他们可以为改变自己,或改变社会做点什么。
我想吴先生来大陆这几天,他周围的人群算是年轻一代里文化层次比较高的了。如果他感觉《读库》此类如论文一样长的文章在这里很多人看的话,很大程度只局限于他周围的一个很特别的小圈子。不信大家每个人可以问问周围的朋友就知道了。而吴先生在国内接触到的层次比较高的知识青年,如果更多的只是拿一些知识标榜,我实在看不出哪里比台湾的年轻人高明了。
其实吴先生在这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中,也无意透露出,觉得台湾经历过经济的大起大落后,现在的人们开始重视很多人文的东西。他希望现阶段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大陆,能在过程中不要再犯他们以前犯过的错误。而我觉得很多错误不仅犯了,而且要比吴先生想象的严重。
游戏中秋
中秋三天,阴冷异常,想去年的国庆都还是暖和的吧,怎么今年就冷得这么早。
第一天下着小雨,两个人穿着短袖短裤就出门了,直奔MOMA,听说是有左小祖咒的签售,想着150一张的CD,就豁出去搞一张吧,国内还真没买过这么贵的。到了MOMA,已经到点了,奇怪着怎么冷冷清清,难道是下雨人少?到门口一问,人说“是明天吧”,才恍然大悟,可怜两人一路冻着,午饭也没吃,虽然不算千里迢迢,但也是饥寒交迫。到库布里克书店取了会暖,心想着要是住这附近就好了,肯定天天来看书。犹豫了会接下来要去哪,最后决定去买游戏碟,回家玩游戏去。
《2011足球经理》和《古剑奇谭》,一人选了一款,吃完饭就回家兴冲冲装上了。第一天晚上玩到3点,第二天睡到中午起来,一看时间,有点来不及了,于是一个建议说干脆不去看左小祖咒了吧,另一个竟然也直接默许。两个人一人守着一台电脑,一句话也不说,各自专注的玩着两个游戏,直到晚上出门觅食。阵阵秋凉的街道上,看周围的景致,好像都有些不真实。一路走着,一路回想还是学生那会儿,有同学在宿舍玩《足球经理》,手里抱个热水壶,拿本高数书,其他人去自习室准备考研,早上出门到晚上回来的时候,那个同学还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不知道那位同学现在还会那样打游戏么?以前暑假那会,每次回家都会去买一张新出的游戏,虽然可能很快就能通关,但拿到手里的那瞬间,会感觉整个暑假又多了一些趣味,还有,寄托。
要不是第三天是中秋,和爸妈有约,可能两人还得玩上一整天吧。